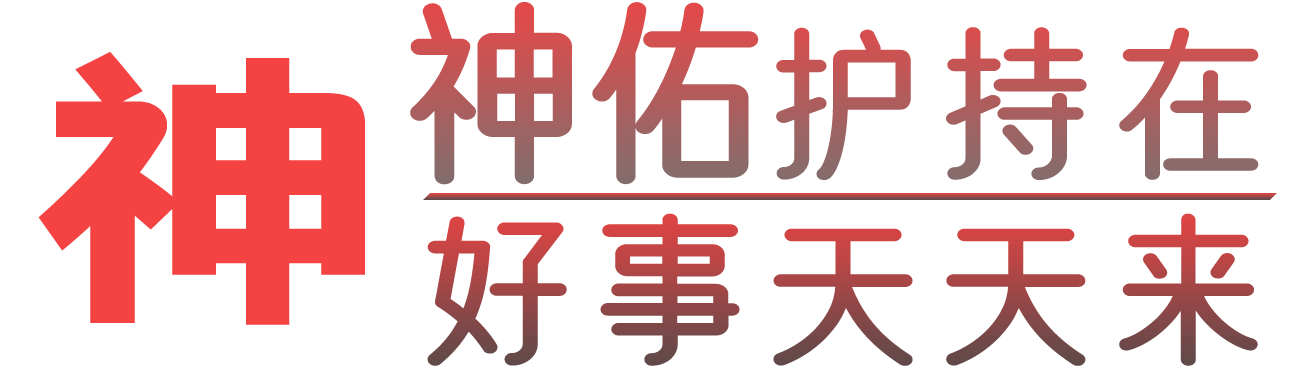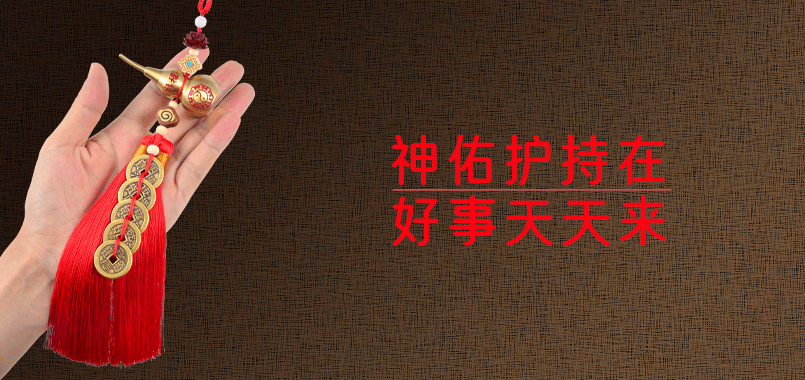京城炙夏寻清凉:道家‘法自然’里的避暑智慧

七月的京城像被架在文火上慢烤的陶瓮,蝉鸣黏在梧桐叶背不肯松口,柏油路泛着恍惚的白汽,连便利店冰柜的冷气都带着股急躁的热意。我站在地铁口等朋友,手机显示地表温度40℃,突然想起上周在什刹海遇到的老茶客——他摇着葵扇坐在廊下,石桌上摆着粗陶碗,碗里的茉莉茶浮着半片鲜荷叶,"小同志,这热啊,越较劲越难受。
说起来我们这代人避暑,总像在和老天爷掰手腕。空调开得越低越好,冰咖啡吨吨灌下,可往往出了空调房就头晕,喝太多冰的胃里像坠着块石头。上个月邻居李姐还跟我抱怨:"我家娃暑假天天窝空调房,这两天总说膝盖凉飕飕的,大夫说寒气淤在体内了。"我们拼命用科技筑造清凉堡垒,却忘了老祖宗早就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写明白:"夏三月,此谓蕃秀,天地气交,万物华实,夜卧早起,无厌于日。"道家讲"法自然",不是让我们硬扛暑热,而是学会顺着自然的脾气来。
记得去年三伏天,我跟着胡同里的王奶奶学了一招"顺时纳凉"。她把竹帘换成新晒的,说是"新竹有清露气";早晨五点就起来扫院子,等太阳爬过屋脊,葡萄架下的石凳早凉透了;午后从不贪睡,煮一壶绿豆百合汤,里面还扔两片薄荷,"这凉是从嗓子眼里慢慢渗出来的,比灌冰可乐舒服多了。"最妙的是傍晚,她搬着藤椅坐在院门口,看穿堂风掀起竹帘,把廊下挂的铜铃吹得丁零响,"你听这风响,比空调声可有意思多了。"
前阵子去西山拜访位研究道家文化的老师,他指着窗外说:"你看那棵老槐树,夏天拼命长叶子给人遮阴,秋天就落得干干净净,这就是'法自然'。人也一样,夏天该出汗就出汗,该早睡就早睡,别跟身体拧着来。"他的书房没装空调,窗台上摆着个青瓷缸,养着几株菖蒲,风穿堂而过时,满屋子都是草叶的清苦香。我在那坐了一下午,竟没觉得热,倒像是被裹在层柔软的凉雾里。
其实最动人的"清凉"不在温度表里。上周暴雨后,我路过玉渊潭,看见几个大爷在廊下下象棋,石桌上的搪瓷杯飘着茉莉香,头发斑白的阿姨举着蒲扇给老伴扇风,嘴里念叨:"刚下过雨,风多凉快,吹吹多舒服。"那一刻突然懂了,道家的避暑智慧从来不是教我们对抗炎热,而是教我们在热浪里找到和自然和解的方式——是清晨的一碗薏米粥,是傍晚的一段穿堂风,是放下手机看云卷云舒的半小时。
你有多久没在晚风里坐一坐了?有多久没闻过雨后青草的味道?当我们不再把清凉当作战利品去争夺,而是像老茶客那样,端起粗陶碗慢慢喝一口凉透的荷叶茶,或许会发现:真正的清凉,从来都在顺应自然的从容里。就像王奶奶说的:"人呐,跟着节气走,比跟着温度计走,舒服多了。"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www.i199.art/daofaziran/228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