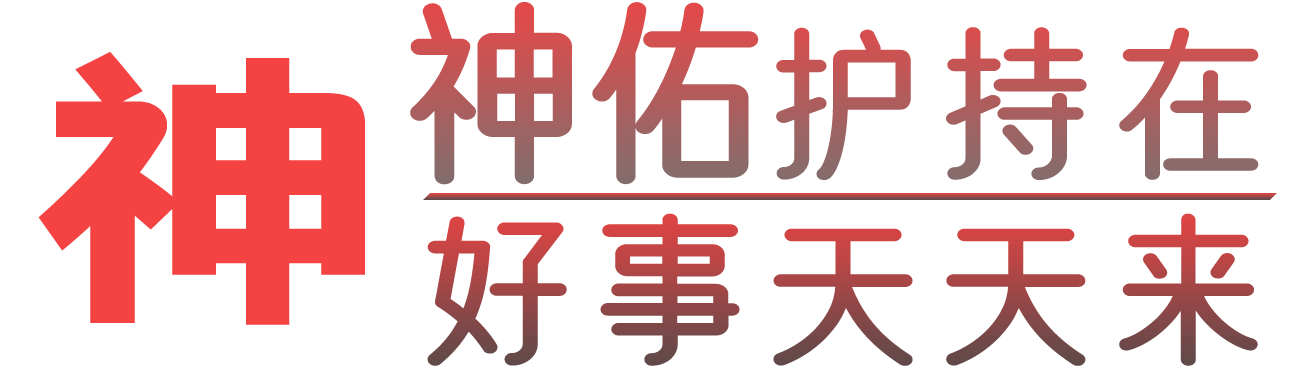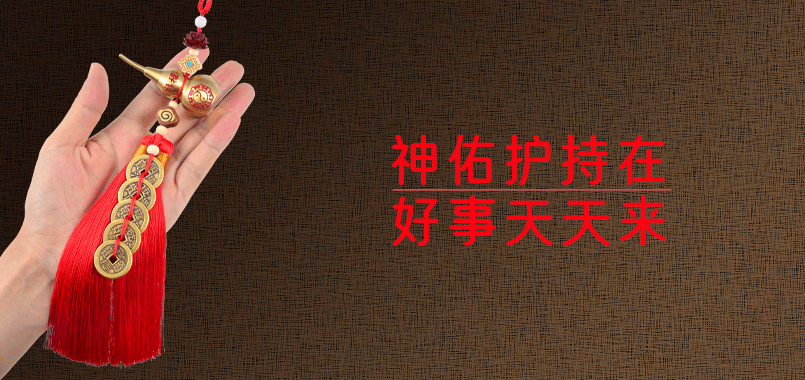非遗绒花:一根铜丝绕出千年宫廷美学,指尖技艺藏着哪些文化密码?

晨雾还未散尽,南京老门东的一间木屋里已飘出细弱的"沙沙"声。68岁的王秀兰坐在藤椅上,老花镜滑到鼻尖,左手捏着半根细如发丝的铜丝,右手的镊子正将一缕淡粉蚕丝往铜丝上缠——这是她做了40年的动作,像在编织春天的影子。
"您看这铜丝,得先在火上烤软,再用牙咬着拉直。"王阿姨突然抬头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,"我师父教我时说,绒花是戴在头上的诗,每根丝都得有温度。"她指节粗大,指甲盖泛着常年接触染料的淡青色,可捏着铜丝的指尖却灵活得像穿针的蝴蝶。
这门让王秀兰痴了一辈子的手艺,最早能追到唐代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里记着"贵妃插鬓,步摇绒花",到了明代,南京绒花已是"匠作局"的贡品,清代更成了后妃们的"头面标配"——故宫藏品里,孝端皇后的凤冠上还缀着绒制的牡丹,历经四百年仍葆着丝绒特有的柔润。
"可别小看这团'软乎乎'的花。"王阿姨抽出一根做好的绒叶,对着光转动,蚕丝纤维折射出细密的光晕,"铜丝是骨架,得绕出花瓣的弧度;蚕丝要染二十多遍,从米白到胭脂红,每遍都得等前层干透。最绝的是'劈丝'——把一根蚕丝劈成十六股,细得能穿过绣花针。"她曾试过用机器代替,可机器劈的丝总带着毛边,"手艺人的气儿,机器学不来。"
绒花里藏着的,远不止手艺的讲究。王阿姨翻出一本旧相册,泛黄的照片里,一位穿旗袍的女子头戴绒制的"岁寒三友","这是我奶奶,1947年结婚时的头花。"她指尖抚过照片,"那时候讲究'无绒花,不成婚'——牡丹是富贵,蝙蝠是福到,石榴是多子,连叶子的数目都有说法:单瓣是正室,双瓣是侧室?不,那是老辈人开玩笑的。"她突然笑出声,"其实就图个吉利,你看现在年轻人结婚,也爱订绒花发簪,说比钻石多了份'活的心意'。"
可这份"活的心意",也曾差点断了线。上世纪90年代,机织绢花涌入市场,绒花成本高、耗时长,渐渐没了销路。王阿姨的作坊最惨时,只剩她和两个徒弟,"有天徒弟说要去电子厂,我攥着没做完的绒梅,突然觉得手在抖——这门手艺要是断在我手里,我怎么去见师父?"她顿了顿,从抽屉里摸出个红布包,里面躺着半朵褪色的绒菊,"这是师父临终前塞给我的,他说'花会谢,可手艺不能谢'。"
转机出现在2018年。某部清宫剧里,女主角头戴绒花的镜头火了,年轻人追着问"这花能买吗"。王阿姨的作坊门口排起了长队,有穿汉服的姑娘,有做珠宝设计的设计师,甚至还有外国留学生来学"绕铜丝"。24岁的小琳就是那时候来的,"第一次见王老师做绒花,她绕出的桃花比真花还水灵,我突然觉得,老手艺也能很时髦。"现在的小琳,能把绒花做到米粒大小,镶在胸针上,"上次有个顾客说,戴着这枚胸针,像是把春天别在了衣服上。"
暮色漫进窗棂时,王阿姨开始做今天最后一朵绒花——是给小琳的订婚礼物,三朵并蒂莲,花瓣用渐变的藕荷色。"你闻闻,蚕丝染了栀子花的香。"她把花递过来,我凑近时,真有一缕若有若无的甜香钻进鼻尖,"以前宫廷里的娘娘们戴绒花,图的是体面;现在的年轻人戴,图的是'我知道它从哪来'。"她望着窗外渐次亮起的灯,声音轻得像飘在空中的蚕丝,"手艺这东西,最怕的是没人记着;最甜的,是有人接着。"
风从门缝里溜进来,吹得案头的绒花轻轻摇晃,像在应和什么。或许这就是绒花藏着的文化密码——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活着的、会呼吸的,从千年前的宫廷,一直活到今天的、我们的指尖。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www.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245.html